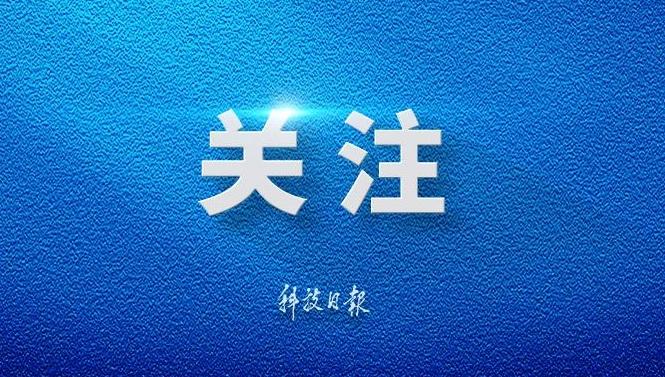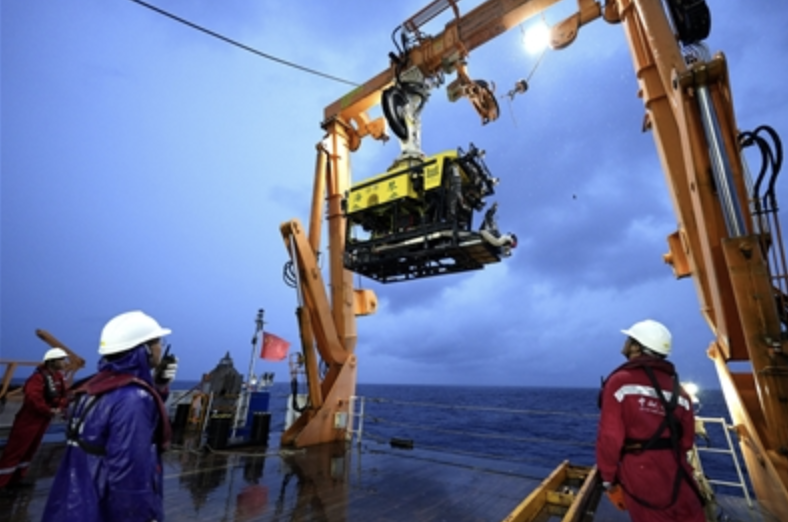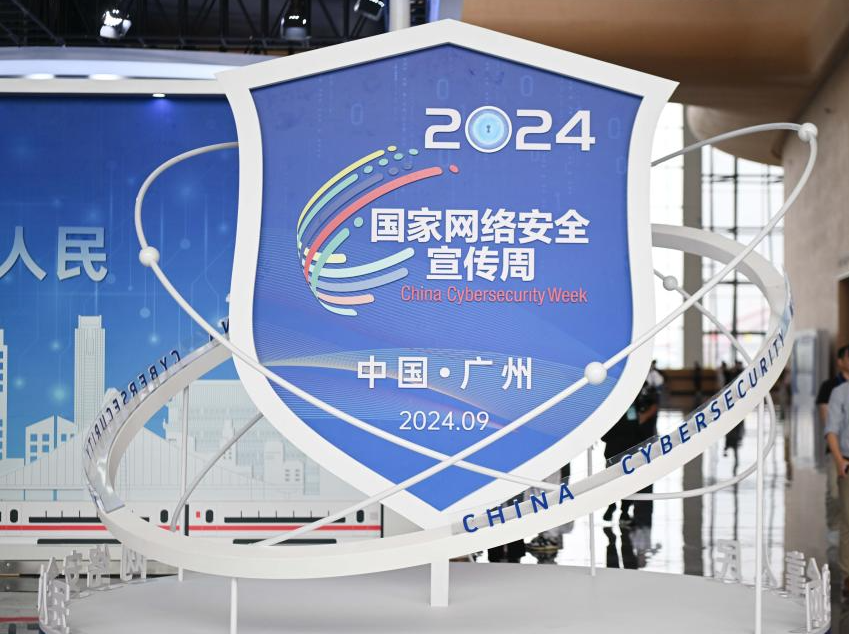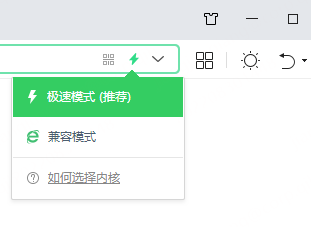科技日報記者 付毅飛
9月5日,北京星河動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河動力”)成功實施谷神星一號(遙十五)運載火箭發(fā)射任務,將開運一號、馭星三號08星、云遙一號27星共3顆衛(wèi)星,以及愛神星留軌試驗平臺送入預定太陽同步軌道。
截至目前,星河動力研制的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已實施21次發(fā)射。其中,今年3月17日和3月21日,該火箭在5天內(nèi)先后實施“一箭八星”和“一箭六星”任務,展示了其密集發(fā)射能力。
高密度發(fā)射之路是怎樣闖出來的?日前,谷神星一號、二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張軍鋒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講述高密度發(fā)射背后的創(chuàng)新與突破。

“航天工程里沒有小問題”
記者:想讓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實現(xiàn)高密度發(fā)射,您和團隊要面對哪些挑戰(zhàn)?
張軍鋒:挑戰(zhàn)主要來自以下三方面。一是產(chǎn)品可靠性。在設計階段,我們需通過多維度仿真模擬與極限工況測試,確保各分系統(tǒng)在復雜太空環(huán)境下的適配性。
二是生產(chǎn)管理和任務統(tǒng)籌。從一年執(zhí)行一次發(fā)射任務到如今高密度發(fā)射,生產(chǎn)管理與任務統(tǒng)籌方面的壓力倍增。這不僅是任務量的簡單疊加,更涉及全鏈條的協(xié)同攻堅。我們需建立穩(wěn)定且有彈性的配套體系,確保發(fā)動機、控制系統(tǒng)等核心部件的產(chǎn)能可以隨發(fā)射頻次同步提升。
三是發(fā)射流程優(yōu)化。我們從火箭進場開始拆解全流程節(jié)點,將傳統(tǒng)準備工作拆解為上百個標準化子步驟,通過數(shù)字化系統(tǒng)實時追蹤每個節(jié)點的完成狀態(tài)。比如,在箭體轉(zhuǎn)運環(huán)節(jié),我們采用自動化導航與定位技術,將對接誤差控制在厘米級,較傳統(tǒng)方式節(jié)省40%的時間。
記者:截至目前,谷神星一號已實施5次海上發(fā)射。研制這款海陸通用火箭有哪些難點?
張軍鋒:海陸通用火箭要同時適應陸地與海上兩種截然不同的發(fā)射環(huán)境,最主要的是要適應海上高溫、高濕、高鹽霧的“三高”環(huán)境并應對高海況帶來的多重挑戰(zhàn)。海上惡劣環(huán)境極易侵蝕箭體結(jié)構、影響電子設備性能,甚至干擾衛(wèi)星載荷的穩(wěn)定性。
對此,我們從兩方面進行突破:一是對箭體進行全密封強化設計,采用特殊防腐涂層與密封材料,提升整體環(huán)境適應性;二是為發(fā)射系統(tǒng)配備智能溫控保溫艙,實時調(diào)節(jié)艙內(nèi)溫濕度,為火箭和衛(wèi)星打造恒溫恒濕的過渡環(huán)境。
記者:從最初立項研制到實現(xiàn)高密度發(fā)射,您和團隊都遇到了哪些難“啃”的“硬骨頭”?
張軍鋒:“硬骨頭”主要集中在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0到1”的階段。2018年星河動力剛成立時,我們團隊連固定的辦公場地都沒有,幾十個人在臨時租來的辦公室里畫圖紙、做仿真。當時,國內(nèi)商業(yè)航天的配套體系還不成熟,很多核心部件找不到供應商。火箭設計方案更是幾易其稿。為了優(yōu)化方案,團隊曾連續(xù)45天泡在實驗室,每天只睡3個小時。2020年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成功首飛那天,火箭沖破云層的瞬間,大家都激動不已。
第二階段是“從1到N”的階段,即從單次發(fā)射邁向高密度發(fā)射。星河動力前3發(fā)火箭發(fā)射間隔比較長,團隊準備時間相對充足。在進入高密度發(fā)射階段后,整個體系都面臨重構。比如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原來單批次零部件生產(chǎn)可以慢慢打磨,現(xiàn)在要同時保障3發(fā)火箭的總裝,供應鏈稍有脫節(jié)就會斷檔。更關鍵的是團隊能力的迭代,原來一個工程師負責一個分系統(tǒng),現(xiàn)在要同時對接3個批次的測試任務。
記者:2023年9月21日,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在九連勝之后遭遇了目前唯一一次發(fā)射失利,當時出了什么問題?此后團隊采取了哪些措施?
張軍鋒:當時,火箭一級發(fā)動機噴管擴張段燒蝕異常,導致火箭姿態(tài)出現(xiàn)異常,最后發(fā)射任務失利。事后,我們立刻啟動歸零程序,組織專家對箭體殘骸進行逐層拆解分析,最終發(fā)現(xiàn)噴管擴張段某一個螺絲孔內(nèi)壁存在細微裂紋。這是供應商在鉆孔時因進給速度控制不當產(chǎn)生的應力損傷。就是這個肉眼難以察覺的缺陷,在高溫高壓環(huán)境中被迅速擴大,導致噴管燒蝕異常,最終引發(fā)姿態(tài)失控。
這次失利給了我們沉重一擊,但也讓我們清醒認識到:航天工程里沒有小問題。過去九連勝讓團隊成員多少有些松懈,當時的工藝文件對螺絲孔加工的進給速度、冷卻方式等細節(jié)規(guī)定得不夠明確。
痛定思痛后,我們從三個維度進行全面整改:一是聯(lián)合相關單位對工藝規(guī)程操作進行優(yōu)化,組織開展相關人員培訓;二是啟動質(zhì)量提升工程,在設計端增加30%的極限工況驗證,驗收端建立“雙人雙機”復核制度;三是改革外協(xié)管理模式,對核心供應商實施“派駐工程師+過程審計”,每季度開展質(zhì)量追溯演練。
“站在‘前輩’肩膀上創(chuàng)新”
記者:請介紹未來一兩年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的任務規(guī)劃。
張軍鋒:未來一兩年,谷神星一號將繼續(xù)深耕商業(yè)發(fā)射市場,預計每年執(zhí)行10發(fā)左右的發(fā)射任務。技術創(chuàng)新方面,我們不會對火箭主體結(jié)構進行顛覆性改動,而是主要以“存量挖潛+功能延伸”為抓手,提升其太空服務能力。
記者:在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日趨成熟的基礎上,星河動力正在研發(fā)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為什么要研發(fā)新火箭?其具備哪些技術特點?
張軍鋒:研制谷神星二號主要是為填補市場運力空白。當前商業(yè)航天市場中,中小型星座的發(fā)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很多客戶需要將1噸左右的載荷送入特定軌道,而且對“專箭發(fā)射”的時效性要求很高。目前我們的產(chǎn)品矩陣里,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主要覆蓋300公斤以下的載荷,智神星一號液體火箭則聚焦2.5噸至7噸的中大型任務,1噸級左右的運力區(qū)間急需填補。研發(fā)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就是為了填補這個空白。
從技術特點來看,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是“站在‘前輩’肩膀上創(chuàng)新”。它繼承了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成熟的技術框架,使研發(fā)風險顯著降低。同時,我們在可靠性上做“加法”,哪怕某一系統(tǒng)出現(xiàn)異常,其他系統(tǒng)能立刻接管控制。陸海通用能力的升級是另一大亮點。相比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的“陸海同型”設計更徹底,一些關鍵技術得到了升級。
最關鍵的創(chuàng)新體現(xiàn)在運載效率上。我們對四級軌姿控系統(tǒng)進行優(yōu)化,使其運載效率比谷神星一號運載火箭提升40%以上。以700公里太陽同步軌道為例,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一次能將4顆250公斤級衛(wèi)星送入不同軌道面,相當于用更少的燃料完成更復雜的部署任務。
記者:目前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的研制進展如何?
張軍鋒:谷神星二號運載火箭的研制工作已開展一年多,整體上進展順利。目前工程研制階段的設計工作已完成,項目正處于單機性能考核與系統(tǒng)集成驗證的關鍵期。這一階段工作就像給一臺精密儀器安裝核心零件,既要確保每個零件運轉(zhuǎn)正常,又要驗證零件組合后的協(xié)同效果。該型火箭計劃今年首飛,年內(nèi)大概會安排兩三次發(fā)射任務,明年我們計劃將發(fā)射頻次提升至5發(fā)至10發(fā)。
記者:目前中國商業(yè)航天發(fā)展已步入快車道,您如何看待其發(fā)展趨勢?
張軍鋒:這幾年中國商業(yè)航天的發(fā)展速度確實令人振奮。從2018年商業(yè)火箭首次嘗試發(fā)射至今,短短幾年間已有多家企業(yè)實現(xiàn)固體、液體火箭入軌,加上國企和混合所有制企業(yè)的全面入局,整個行業(yè)形成了“多元主體競合”的格局。這種態(tài)勢背后,是國家政策的持續(xù)加碼——從商業(yè)航天發(fā)射場的布局到太空資源利用的規(guī)劃,再到地方政府設立的專項扶持基金,都為行業(yè)注入了強勁動力。
從發(fā)展路徑看,中國商業(yè)航天正在從“單點突破”邁向“系統(tǒng)成熟”。早期大家更關注“有沒有火箭能上天”,現(xiàn)在則聚焦“如何更高效、更低成本地把衛(wèi)星送入預定軌道”。我預測,未來3到5年,隨著低軌衛(wèi)星星座的密集組網(wǎng),商業(yè)發(fā)射需求或?qū)⒈l(fā),進一步倒逼行業(yè)提升效率。
“多往車間跑、多去試驗場看”
記者:請您介紹下所在研發(fā)團隊。
張軍鋒:目前我們團隊已經(jīng)接近500人,覆蓋火箭總體設計、動力系統(tǒng)、控制系統(tǒng)、結(jié)構機構、總裝測試等專業(yè)。回想2018年公司剛成立時,整個團隊只有幾十人,每個專業(yè)小組只有一兩人。
那時最大的挑戰(zhàn)是“觀念融合”。團隊成員背景不同,工作思路各異。記得討論箭體連接方式時,老專家堅持用螺栓剛性連接,而年輕工程師主張用柔性鉸鏈減震,雙方爭論不下。不過,這種“在爭論中找共識”的氛圍,反而讓團隊成員快速熟悉,逐漸擰成一股繩。
隨著公司不斷發(fā)展,我們團隊規(guī)模擴大。這幾年我們把招聘重點轉(zhuǎn)向應屆生,2024年入職的120名新員工,大多是應屆畢業(yè)生。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成熟人才,而是因為已經(jīng)搭建起“導師帶徒+項目實戰(zhàn)”的培養(yǎng)體系:新員工先在設計崗跟導師做半年仿真,再到試驗場參與火箭試車,最后獨立負責某個分系統(tǒng)的測試任務。現(xiàn)在團隊里30歲左右的青年骨干占比超過40%。
記者:您如何培養(yǎng)年輕科研人才?
張軍鋒:在培養(yǎng)年輕科研人才方面,我摸索出一套模式。剛?cè)肼毜哪贻p人,理論基礎扎實但工程經(jīng)驗欠缺。我們先從“補短板”開始,針對不同崗位設計“定制化課程包”。比如結(jié)構設計崗的年輕人,除了要學有限元分析軟件的進階用法,還要系統(tǒng)掌握材料力學在箭體承力分析中的實際應用。
不過,真正的成長,一定是在工程實踐里“摔打”出來的。我們推行“項目帶教制”,讓每位年輕人跟著具體任務走,從方案論證階段就參與進來。比如,去年入職的幾名應屆生跟著我們團隊,從畫第一張控制流程圖,到記錄地面試車參數(shù),再到在發(fā)射場做箭上設備調(diào)試,每個環(huán)節(jié)都盡可能讓他們參與。
我的成長也離不開工程實踐。剛上班時,一位學長給了我一份總體參數(shù)表,上面寫了幾十種設備。當時,我看著那些名稱根本沒概念,也記不住。后來,我去總裝現(xiàn)場學習了幾天,很快就把這些設備名稱記熟了,還把它們在火箭上的實際用途、工作方式對應起來,對它們的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現(xiàn)在我要求年輕人多往車間跑、多去試驗場看。
記者:為滿足航天未來發(fā)展要求,您認為青年航天人才應具備哪些素質(zhì)和能力?
張軍鋒:航天行業(yè)門檻很高,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yè),首先理論基礎要扎實,同時必須具備嚴慎細實的工作作風。另外,要具備系統(tǒng)協(xié)作能力。一枚火箭涉及上百個分系統(tǒng),如果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很容易出現(xiàn)銜接漏洞,優(yōu)秀的青年人才得有“全局觀”。
此外,年輕人還要有敢闖敢試的創(chuàng)新魄力與持續(xù)學習的意識。商業(yè)航天技術迭代快,年輕人不能滿足于“按流程做事”。同時,要盯著國際前沿,知道同行在做什么、技術拐點可能出現(xiàn)在哪里,才能避免閉門造車。
記者手記
2018年10月,藍箭航天空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朱雀一號火箭從甘肅酒泉升空,雖然未能將衛(wèi)星送入預定軌道,但這成為我國商業(yè)火箭首次軌道發(fā)射嘗試。
彼時,星河動力成立僅8個月,行業(yè)內(nèi)知道張軍鋒的人并不多。沒人知道,這個后來帶領團隊闖過無數(shù)難關的總設計師,當時正對著滿桌的火箭方案草稿,琢磨著如何在一片空白中蹚出一條路。
再見張軍鋒,是在2020年11月谷神星一號首飛成功后。那天火箭沖破云層,將天啟星座十一星送入500公里太陽同步軌道。人群中的張軍鋒沒有太多激動的表情,只是反復核對數(shù)據(jù)。
之后幾年,谷神星一號成了商業(yè)航天的“明星”。從陸地發(fā)射到海上“一箭四星”,從單次發(fā)射到5天內(nèi)連續(xù)完成“一箭八星”“一箭六星”,九連勝的戰(zhàn)績讓業(yè)內(nèi)驚嘆。可2023年9月21日,一次發(fā)射意外打破了這份順遂。那天的張軍鋒,眼中滿是疲憊,卻沒回避任何問題。
聊起那次失利,張軍鋒總說“是警鐘,也是轉(zhuǎn)機”。之后的日子里,他帶著團隊重新梳理工藝規(guī)程,在設計端增加30%的極限工況驗證,在驗收端建立“雙人雙機”復核制度。
現(xiàn)在的張軍鋒,肩上多了谷神星二號的研發(fā)任務。和記者聊起這款新火箭,他會翻出手機里的測試視頻,指著屏幕里的箭體說個不停。
從首飛成功的忐忑,到失利后的重整旗鼓,張軍鋒的故事,其實是中國商業(yè)航天的縮影——沒有捷徑,只有“啃硬骨頭”的執(zhí)著。而中國商業(yè)航天的穩(wěn)步發(fā)展,正是由無數(shù)個張軍鋒托舉而成。




 網(wǎng)友評論
網(wǎng)友評論